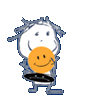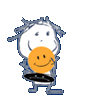我在民國八十三年得了憂鬱症而不自覺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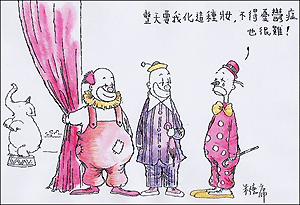 當時整個人脫序、失能,身上從頭到腳都覺得不舒服,頭暈、胸悶、心悸、血壓莫名奇妙忽高忽低,腸胃消化不良等。情緒上變得很低落,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,美食當前味如嚼蠟,每到夜晚更是輾轉難眠。家人陪伴四處求醫未果,身心備受煎熬的我,逐漸感到人生乏味,了無生趣;在一個機緣之下得以找專業精神科醫師,經診斷才確定是得到憂鬱症。 當時整個人脫序、失能,身上從頭到腳都覺得不舒服,頭暈、胸悶、心悸、血壓莫名奇妙忽高忽低,腸胃消化不良等。情緒上變得很低落,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,美食當前味如嚼蠟,每到夜晚更是輾轉難眠。家人陪伴四處求醫未果,身心備受煎熬的我,逐漸感到人生乏味,了無生趣;在一個機緣之下得以找專業精神科醫師,經診斷才確定是得到憂鬱症。
從此展開治療歷程,首先就是服用抗憂鬱劑,先讓症狀緩解。第二步則是參加十二週的團體心理治療。當我第一次踏進團療教室,發現每一位病友述說自己發病和就醫過程,莫不百感交集、淚如雨下,正是我內心的寫照。他們的每一個症狀我都有,陌生的臉孔因著相似的痛苦,而變得熟悉起來。
第二週上課,原本有苦說不出的我,開始可以含淚說出自己的病情和心情。病友們轉而關懷、安慰我,因為同病相憐而同舟共濟,在這個小小的教室裡,每個人都發覺自己一點也不孤單。
最特別的是,團療中的幾位志工都是過來人,他們適時現身說法、分享經驗,看到他們容光煥發、充滿自信的樣子,就好像一盞明燈,讓我們看到了希望。每週一次的上課,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為了徹底打擊憂鬱症,找出源頭,也就是錯誤的信念和認知。團療中強調認知行為的改變,重建一套新的思考和行為模式,頑強的舊習性要破除實不容易,必須經由醫師不斷點醒、灌施、耳提面命。幸而團療是以團體互動方式進行,彼此成為別人鏡子,可謂事半功倍。
治療憂鬱症的最高目標不只是「康復」而是「改變」。我學到凡事往好的方面想,有了正面的思考就會有正向的人生觀,本來以為大難臨頭,世界末日,只要轉個彎,換個想法,也可以四兩撥千斤。
作者:郭來榮 現為董氏基金會心理健康促進委員
2003/6/17 下午 11:37:06
|